现场概况-第三天 中美高级精神分析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春季班第三季第三期)
现场概况-第三天
中美高级精神分析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
(春季班第三季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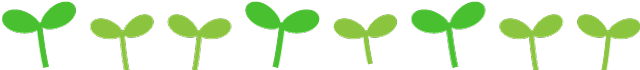
1
午间演讲

PTSD与CPTSD的诊断与心理病理学
主讲:童俊教授
开场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疾病PTSD,特别是汶川地震以后。我今天要讲复杂性的PTSD。
新的DSM系统将创伤分为:
1.创伤与压力相关障碍
2.解离障碍
3.躯体症状与相关障碍
创伤的实质
创伤的瞬间,受害者被压倒性的力量推至无助的境地。创伤性事件淹没了常规的让人体验到的控制感、情感连接和生命意义的照顾系统,并给人留下创伤性记忆。
创伤记忆:
精神病学家玛迪·霍洛维兹(Mardi Horowitz)假定了一个“完结原则”,这个原则认为“人类思想中具有处理新信息的本能,使得这些新信息能够适应自我和世界的规划”。这个“完结原则”能让人体验到控制感、情感连接和生命意义。
创伤破坏了这些“内在规划”,使人类这种处理新信息的本能遭到破坏,未被完结也不被同化的创伤性体验被储存在一种特殊的“活跃记忆”中,这就是创伤性记忆。
强迫性重复:
这种记忆有“一种本能的倾向要重复所记忆的内容”。只有当创伤的受害者重建那些被创伤破坏的处理信息的本能,为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发展出新的精神的“内在规划”时,创伤才能得到解决。
为什么重复?
学者们倾向于将创伤事件是否对人导致伤害要看承受创伤事件的个体是否“超载”。这种“超载”必须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而被粉碎、被清除。即每次重复患者都潜意识地希望是对这种超载的卸载,或称为一种脱敏。患者为了重建被破坏的控制感,会去依附那种自己知道的魔鬼,患者对这种预先设想的魔鬼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哪怕这种方法是破坏性的,但会让患者感到能去控制。患者也可以在这种重复中寻求一种需要但丧失的关系等等。
通俗地讲创伤的受害者都会将受难归咎成自己不好,他们幻想如果我做的足够好,灾难就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像如此之坏的事情,如果我做得比别人要求我的更好,就不可能发生”。期待的是我这次一定要做的比上次好!
什么是强迫性重复的驱动力?
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家保罗·拉塞尔(PaulRussell)将创伤的情感体验,而不是创伤的认知体验理解为强迫性重复的驱使力量。被重现的是“人为了修复伤害而需要得到感受的内容”。他将强迫性重复看作是再现和掌握创伤时刻压倒性感受的尝试。
创伤后应激障碍
1980年,当创伤后应激障碍首次被引入到诊断手册当中时,美国精神病协会将创伤性事件描述为“超出常规人类体验的范畴之外”。创伤性事件之所以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不是因为他们很少发生,而是因为他们颠覆了人类对生活的常规适应。心理创伤通常的背景是“强烈的恐惧、无助、失控和被消灭的威胁”的感受。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众多症状可以被分为三类。我们称之为“高唤起”、“闯入性”和“压缩”。高唤起反映了对危险持续地准备;闯入性反映了创伤时刻留下的永久的印象;压缩反映了投降者麻木的反应。
创伤性患者在高唤起和麻木的两极之间摇摆。他们被困在强烈情绪的冲击、压倒性感受和没有任何感觉的贫瘠状态之间,被困在易激惹、冲动性行动和行为的完全抑制之间。由这些阶段性变化所产生的不稳定进一步加重了受创伤的人的不可预知感和无助感。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临床发现有些慢性创伤后幸存者的症状不同于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的慢性创伤性环境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童年生活中。精神科对这类患者的诊断似乎缺乏一种整合性的能力,即是将他们的症状、人格缺陷、与他们长期的起自幼年的慢性创伤性环境相联系的能力。
缺少一个精确和完整的诊断概念对于治疗有着严重的后果,因为患者当前症状和创伤经验的联系经常会被遗忘。将患者强行崁入既有的诊断架构至少会导致对于患者当前问题的片面理解和治疗的碎片化。
近二十多年来,在欧美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界开始将上述这类患者用一个新的诊断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来概括。同时,为了区分起见,他们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称作Ⅰ型创伤,将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称作Ⅱ型创伤。
CPTSD的症状包括PTSD的三个核心症子集状和另外三种界定为自我组织障碍(DSO)的症状:(1)情感性调节障碍(AD)、(2)负性自我概念(低自我概念)(NSC)、(3)人际关系障碍(DR)。
当我们看见一个患者带着如下不止一个诊断时,如边缘性人格障碍、躯体化障碍、多种人格障碍等,我们就要警惕患者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这三种障碍的一个共同因素是他们都有着儿童创伤史。所有这三种障碍都和高水平催眠易感性或者解离有关,所有这三种障碍在亲密关系上也有着共同的特征性的困难。
理解儿童期创伤在发展中的角色和在这些严重障碍中的角色能够影响治疗的各个方面。这种理解提供了形成一个协作性治疗联盟的基础,使幸存者对于过去事件的情感反应正常化和稳定化,幸存者认识到这些反应只是过去一些错误的适应。而且如果治疗师理解幸存者难以建立关系,并且倾向于重复成为受害者,就能有效的避免原初创伤在治疗关系中不知情地重新出现。
提问环节
学员提问:童老师,您会直接建议病人去完成上坟这样仪式吗?童俊教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要看什么病人,我门诊的病人,他们要花很长时间去挂我的号才能来。我有很多一次session要处理的病人,要去解决问题。有一个治疗师跟我说,我给他做一次session,他一年都可以呼吸了,过了一年再来找我。
不是我心理治疗的病人,我要直接建议他去上坟。我门诊处理过很多这样的病人,我没有精力去处理他们,他们也没有钱来做心理治疗。有很多死了人,不去上坟的,明显没有完成哀悼,我会建议他们去上坟。我长程的病人,会自己去上坟的,不需要我建议。
为什么建议他们去上坟呢?不去上坟是应对丧失的原始方式。死去的亲人就埋藏在他们心里,和他共生在一起。丧失的客体就镶嵌在他们的人格当中。去上坟这样的一个仪式,可以从外在影响内在。
2
晚间演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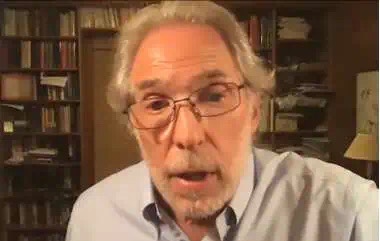
一个自体/多个自体:压抑和解离
主讲:Doug Chavis
翻译:王晓彦
压抑和解离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吗?还是简单的一方是另一方的子分类?例如,解离是否是恋物癖对现实进行否认时使用的防御机制的别称 (弗洛伊德,1927),然后被理解为单一自我的分裂(弗洛伊德,1941)?伊格尔(2000)发现了解离和压抑之间的本质区别。压抑包含了一个统一的自体或自我或身份,某些潜意识心理内容由于心理冲突、恐惧和禁忌而被排除在意识之外,或从意识中分裂出去。而在解离中,潜意识内容涉及的是互不兼容的多重自体、多重自我、多重身份。解离的问题经常看似是存在多重意识。
美国的关系-人际学派继承了沙利文的传统,尤其是米歇尔(1993),布朗伯格 (1998, 2006, 2011)以及多尼尔·斯特恩(1997)。斯特恩阐述了有关“未成形的经验”的概念,指的是一种原始心理状态,从未明确表示要进入防御机制,它是我们的一种非常自然的存在方式,是所有思维的原始矩阵。解离描述了言语经验和这一未成形地带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有关自我的分裂的概念认为,是自我分裂了。其他理论家们关注的是自体的建构或分离的根源(例如,科胡特)或自体是多重的(例如布朗伯格)。米歇尔(1993)阐述了两条隐喻链,构成了关于自体的思考:空间主题和时间主题。空间主题假设自体是有层次的,单一且连续的。时间主题构成了一个多重的、不连续的自我。米歇尔认为二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了解每一个隐喻中冲突所处的位置是有帮助的。在空间隐喻中,冲突存在于统一自体的不同部分,或许代表着本我、自我和超我。在时间隐喻中,冲突存在于不同版本的自体中,或者自体被解离阻碍了。
布朗伯格(2011)将发展性精神分析,创伤学和神经科学的知识与关系-人际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了。他将“心理”理解为一种伴随着“存在或不存在内在心理冲突的辩证关系中的解离过程”的一种自体状态结构(p.68)。自体状态被定义为“个体化的模块…每一个模块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结构、信仰、主导情感和心情、获取记忆技能、行为、价值观、行动以及调节生理学”(p.73)。未识别的自体状态所导致的发展性创伤,成为了解离的结构。无人能例外。在沙利文之后,他表示这些解离的自体状态被体验为“非我”的元素。由于冲突不仅仅是自体状态能够被识别以及各种状态之间彼此能够“对话”所造成的,因此心理功能就不仅仅建立在冲突之上。冲突很可能只是伴随着解离状态的解除而达到的发展性结果。布朗伯格认为,无法管理、调节或体验冲突预示着解离过程的发生,以及多重自体过程的来临。他相信治疗情境中的任务在于帮助这些自体识别彼此。一旦这些自体能够识别彼此的存在,并理解彼此在表达什么,做什么,那么真正的冲突就有消解的可能了。冲突是发展的结果,存在于非解离的更加统一的自体中。所有的自体或冲突的方面都必须为了形成冲突而暂时同时存在。
人际学派和婴儿观察者们比如毕比和拉赫曼,里昂-露丝,斯特恩,以及依恋研究,都有共同的兴趣。随着对依恋紊乱模式的发现(梅因和所罗门,1986),对解离这一概念也有了新的理解和突破。解离成为了一个可被循证测量的特征,并被发现是紊乱依恋的特征之一,在学步儿期、青春期和成年早期都表现出突出的令人吃惊的连贯性。这一研究以及关系-人际学派日益凸显的影响,导致解离的概念在过去的30年间重新获得了精神分析领域的兴趣。这是关系学派、发展心理学家、依恋理论家、创伤心理学家们产生交集之处。放在依恋动力学的背景中来看,随着关系创伤概念的引入,以及人们认识到依恋动力在现代生活中的普遍性,解离的概念成为了关键的精神分析概念。
在调节恐惧和威胁反应机制中,依恋系统至关重要。如果这些反应机制无法得到调节,那么孩子将难以将注意力从恐惧/威胁中转移开来,聚焦于探索和玩耍。里昂·露丝(2016)的报告中指出,对哺乳动物的神经递质系统的多项研究都发现了依恋系统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调节。的确,依恋系统对恐惧、压力以及威胁的调节,还有生命早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启动,可能是依恋效应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高风险人群中,发现儿童群体中有80%是紊乱型依恋(DA),而低风险人群样本中这一比例为15%。通过解离体验量表(DES)识别解离症状发现样本的5-15%有罹患解离障碍的风险。解离体验量表(DES)由伯恩斯坦和普特南(1986)编制,在这些研究中广为使用。在这个筛选工具中有28个项目,研究的行为诸如:待在车里,想不起旅途的某一段,在倾听别人但却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在自己的财物里发现了一些新的物品并且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出现在那儿的,发现你自己在一个地方但却想不起来自己怎么到那里去的,产生不确定某种经历是否真的发生过的体验,等等。
鲍尔比(1973)认为婴儿可能内化了他们所处的依恋关系中的解离或未经整合的内在工作模式。梅因和所罗门(1990)记录了暴露在陌生情境中的婴儿在需要得到安抚时表现出的矛盾、困惑以及迷茫的行为。元分析显示,紊乱型依恋(DA)与父母的虐待,母婴互动障碍与儿童期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麦迪根等,2006;范伊泽多恩等,1999)。廖蒂注意到DA的整合困难与成人的解离问题之间存在相似性。奥佳华等(1997)报告了一个长达20年的纵向研究,该研究涉及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126个婴儿。他们在研究中发现DA以及生命*初的两年里照顾者情绪上的无能是成年早期解离的强预测因子,而早年的躯体虐待因素并没有增加对解离的预测性。
杜特拉等(2009)报告了另一项研究的结果,该研究涵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56名婴儿,研究跨度从被试的婴儿期直到被试年满19岁。预测手段包括:测量婴儿18个月大时的依恋紊乱,测量婴儿12个月大时母婴互动的性质,测量婴儿18个月大时的母婴沟通受损情况。*后的这个测量手段发现了母婴沟通受损的5种子类型:“①情感沟通错误(例如,给出矛盾的线索;没有回应或对清晰的婴儿信号给与了不恰当的回应),②角色混淆(例如,自体相关的性行为),③消极-侵入性行为(例如,言语或躯体的侵入性)④恐惧导向的行为(例如,表现的被婴儿吓到:无目的的漫游),⑤退缩(例如,对婴儿不热情:当婴儿接近时退后)”。
他们发现对早年养育的测量能够显著预测后期的解离,而对虐待的测量则不能。有趣的是,对后期解离*强有力的预测因子是沟通受损的程度、家庭中缺乏积极情感的卷入,母亲情感的平淡,以及言语虐待。和之前的研究不同,躯体创伤并不能解释解离中存在的大部分的显著差异。
........
3个临床案例(略)
以上这些病人都有一些共同点。
1.这些病人卷入一些让他们感到不受自己控制或者至少不受说话的自我的控制的行为并不罕见。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或“损失时间”、失去控制,或至少不受说话的自我的控制并不罕见。
2. 这些病人都存在不同的或解离的意识状态:有关特定生活方式的记忆受损,成瘾状态,通过看视频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中,等等。
3. 这些病人都有交替的自体结构,能够和分析师建立起不同的移情关系。
4. 当分析师发现病人的多重自体结构的存在,观察到病人有很多面,而有些面似乎不能够或不愿意交谈,并且指出倾听病人的这些面很重要,这样做对于这些病人而言已经被证明有帮助。这一技术起源于对解离性身份障碍的治疗(克鲁夫特2006)。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对明显不是DID的病人的有用性。这些病人看起来似乎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使用多重自体的概念,作为探索他们的不同面或人格化冲突的方式,他们似乎有能力将他们的不同面体验为交替自体。由于交替自体并不是短暂存在的,因此冲突是不存在的,它们被人格化了。这代表了他们现实生活经历的一个维度。只有当化身们能够交谈并承认其他化身的存在,真正的冲突才能消解。
我希望这能够阐释如何运用多重自体理论充分的理解一个大范围里有着解离问题的病人。这源于创造有凝聚力的自体感觉所必需的综合功能,也源于我们对在不同依恋模式下自体构造演变的理解。
问答环节
学员提问1:有关杜特拉的研究(早期母婴沟通和青春期解离症状的相关性),我想问一下,这些人的解离症状是在青春期开始出现的吗?还是研究者刚好是选取了青少年来研究?
Doug Chavis:不是从青春期才开始的,是在婴儿期就开始了,至少是在6个月到10个月或者到12个月大的时候,从这些婴儿的一些不一致、不协调的反应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比方说有些婴儿他一边要黏着妈妈,但是他一边在哭,所以这个时候这样一种差异的反应,就开始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解离的反应,而这种解离的倾向或者这种解离的行为,在一岁的时候开始形成,然后可以一直延续到成年时期。这些都是有一些阶段性的研究已经证实了。
学员提问2:刚才讲到DID和MPD都是多重人格,两者有什么区别?
Doug Chavis:没有区别,是指的同一个现象。在一个自体人格状态的连续谱里,多重人格就像是在连续谱的一端,*靠近极端的一端,这一端表明个体他存在着不同的、独立存在的、多重的自体状态,而在另一端,个体是一个整合的、统一的自体状态,你在跟这样的人交谈的时候,你也不会发现他有这样的解离倾向。
学员提问3:文中提到的母婴沟通受损的5种子类型之二“角色混肴”(例如自体相关的性行为)是什么意思?
Doug Chavis:这里指的是妈妈性欲化了她和婴儿的关系,她对婴儿的反应就像是婴儿对她而言是一个性感的个体一样,或者说婴儿的一些行为,总是会激发妈妈的一些性欲化的东西。所以这个婴儿形成一个整合自体的能力,取决于妈妈她有没有能力去心智化或者去识别婴儿很多的情感或者是行为,比方说婴儿的攻击性,他对于触碰的需要,他对关注的需要,他的恐惧等等。如果这个妈妈她能够识别越多婴儿的这些情绪状态行为,那么这个婴儿就可以发展出越整合的自体;但是如果妈妈的这种能力是受损的,那么这个婴儿就有很大的概率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整合的自体,那么他就更有可能是解离的,他的自体会有更多解离的状态。
3
晚间演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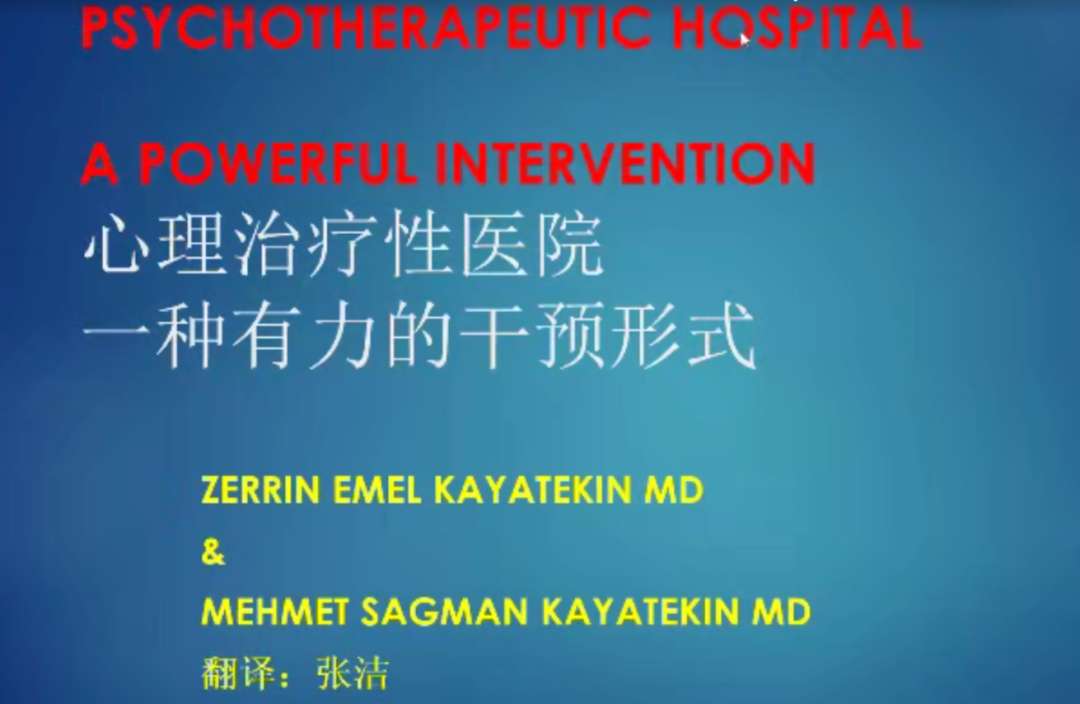
心理治疗性医院:一种有力的干预形式
主讲:Zerrin Emel Kayatekin
翻译:张洁
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再次相遇,虽然我们并不是地面上的课程,而是在网上见,但还是非常开心。我这次演讲的题目是心理治疗性医院,它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干预形式。
首先在讲座开始的时候,我想先澄清一下我这里所说的心理治疗性医院,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熟知的那种精神卫生医院是不一样的两种机构。我这里说的心理治疗性医院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机构。
作为**工作者,我们都受过相关的训练,所以我们对这种一对一的治疗、家庭治疗、小组治疗以及在精神专科医院的这种住院治疗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想大部分人可能对我今天所提的概念“心理治疗性医院”并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我们在通常的训练当中不会涉及到这种方式。
心理治疗性的医院,它其实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世界上**个心理治疗性医院是由Ernst Simmel于1920年代中期创立。Simmel发现,患者呈现出的神经症,常常是家庭的集体性神经症的一种症状,而在病人的分析当中的任何行为都会在重要他人的精神生活当中有着相对应的行为。
那么在我们治疗病人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个病人的治愈,就会导致他身边周围的人的症状也跟着好转,周围的人也跟着被治愈了。但是更常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当病人逐渐好转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却表现出对他好转的一种阻抗,也就是说其实他周围的其他人是不想让他被治愈的,或者是恐惧他的改变,这是Simmel的一些临床发现。
这个其实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些现象,如果我们做过家庭治疗的话,会发现有一些家庭会把病人设定为或者认同为“病人就是一个病人”,然后不想让病人好转起来。虽然他们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个病人有所改变、好转起来,但是同时整个家庭系统又是非常停滞的、不变的,这个时候病人就很难去好转。我们还记得昨天晚间讲座提到的克里斯汀的个案,我们会在个案里面发现他整个家庭的动力系统是非常有问题的,有严重的问题,这就导致了病人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家庭却只希望把这个病人看成是唯一的问题,只希望病人去进行改变,而不去做一些家庭整体系统性的改变,所以他们之前的家庭治疗进行了两次,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所以如果家庭的系统不变,只希望病人一个人去改变,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Simmel建议,这些类型的病人必须在精神分析性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在这样的场所里,病人并不仅仅是跟他的分析师发生一对一的关系,而是整个医院或者诊所都参与到病人的治疗当中来,都在发挥作用。在这里面,病人会跟各种各样的人建立关系,比如说一个护士,对于病人而言,可能是被病人移情为母亲;那么一个医生可能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其他的病人会扮演兄弟姐妹的角色,所以在病人当下的生活当中,好像重现了他既往生活当中的重要他人和重要的关系。所以根据Simmel的说法,这样的一个机构就像是一个“幻影的世界”(the phantom world),它重现了病人各种各样重要的客体关系,就在医院里面都得到呈现,这也给病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在医院里面去对他既往的客体关系进行一些重建。
但是很遗憾的是,世界上**个心理治疗性的医院没有能够存在很久,因为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后来很快就被关掉了,但是这个开创了一个先例,之后不久世界各地就逐渐陆续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心理治疗性医院,如Menninger、Riggs和Chestnut Lodge。与那些会影响病人与社区联结的大型公立医院不同,这些私立医院是开放式的,目的是在一个治疗环境中为少数病人提供,且不使他们脱离社会的日常生活。这些机构教会了我们很多关于人类心理和人类关系的知识。
Menninger康复中心是*具影响力的心理治疗性医院之一,1925年创建时是一家小型诊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治疗中心,一个培养许多代临床工作者的中心。到1990年代末,Menninger康复中心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的经济转型带来了管理式医疗,这像海啸一样冲击着美国医学界。2003年,Menninger基金会解散,Menninger康复中心规模缩小,成为著名的医疗体系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附属机构,后来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本报告主要集中介绍现代的Menninger康复中心,在某些方面并不同于1950年代,但仍然是业界排名*好的医院之一。尽管如此,也许她的独特性在这个排名系统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认可,因为Menninger与一些综合性精神病医院,比如Mayo诊所、大众综合医院相比,是一家专科医院,一家心理治疗性医院。作为一家专科医院,Menninger的治疗范围缩小了,但也使她立足于此,在像Menninger这样的地方,某些疾病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
从现在起,我们将用医院和住院治疗代替心理治疗性医院或心理治疗性住院治疗,以节省篇幅。曾经在Menninger工作过或接受过治疗的临床工作者和病人都认识到了这种干预形式的巨大威力,但大多数人都很难用一种连贯的方式来阐述它是如何实现的。在这篇演讲中,我们会介绍一个聚焦住院治疗的理论。
关于住院治疗的抱持/涵容/自我建构功能都有很好的阐述,客体关系和依恋理论也被广泛引用。在这篇演讲中,我们想回顾一下这样的理论架构中较少被阐述的方面,并提出我们在这些医院工作多年后的观察/想法。
当病人入院时,他/她会被分配到一个团队中,并加入一个同伴小组。他/她还同时开始接受密集的、多层次的干预,个体治疗、家庭治疗、团体治疗、强化护理、追踪、休闲活动等等,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都可能具有同等的治疗价值。住院治疗理论大多围绕着什么是有效干预展开的。一些人建议个体治疗,另一些人则强调另一个场所是*有效的干预措施。我们在医院反复观察到的是,这些方式都不是持续*有效的干预措施,重要性因病人而异,可能会在同一病人住院期间发生变化。有时个体治疗变得更重要,有时家庭治疗成为焦点,而有时是同伴互动。在个体治疗中难以表达自己的病人可以在艺术治疗或音乐治疗中表达自己,这反过来又可以为个体治疗提供动力。在个别治疗中无法交谈的病人可能会与护士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护士可能会帮助病人在治疗的其他方面感到更舒服。这些多途径的干预具有同等的治疗价值(且摆动不定),并且具有相互增强的能力,“多潜能性(pluripotentiality)”。
住院治疗的焦点是我们和病人的自我,个人和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因为在随时间而发展的关系中我们逐渐获得理解,因为我们有时间和兴趣这样做。在医院里,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和病人,有自己明确的角色,但在系统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许多共同点,不像其他医院,如急性精神病院或公立医院,对病人和工作人员角色的明确界定。我们共用同一个自助餐厅/健身房,我们每周共同参加社区会议,共同出席才艺表演,每天进行多次非正式的互动,在这里我们都能展现出我们平凡的一面,并有机会看到彼此,不仅是医生或病人,而且是普通人。
由工作人员和病人组成的环境中,允许发展紧张而独特的个人关系,以及复杂的团体动力。这些多个场所提供了涵容、安全感、归属感、分享、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所有这些都写得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场所创造了发展多重移情/反移情关系(以及多重再现)的机会,不仅是在病人和治疗师之间,而且是在与几个工作人员和同伴之间,使病人能够尽可能复杂地重现他过去人际关系的脚本(自体-客体/群体代表性脚本),在此时此地作为对过去的重复,并希望能够重建、重新解释和修复过去。
当我们采访病人时,我们可能会获得关于病人的广泛信息,然而,我们了解他/她是如何将自己与我们的关系和环境联系起来的,这就是我们如何充分理解病人,“从内心深处”,从我们的反移情和环境的反应之中。
另一个重要的资源是病人和他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团队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医院和家庭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通过这些关系获得了多层次的信息进行比较,而不是仅仅通过与病人谈话获得的二维信息。
在医院里,我们不仅要和移情工作,而且要直接和父母一起工作,父母是移情脚本的原始演员。在医院里,我们把过去的父母带到当下,直接在此时此地处理这段关系,并直接解决双方的防御和所有相关方的严重焦虑,这对防止“消极治疗结果”或“消极治疗反应”非常有帮助。
总之,医院治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一个语境中,实际上是在多个语境中去看病人,他在这个新的允许改进和修复的场所重复他的内在客体关系脚本。正如M.S.Kayatekin博士指出的,在医院里,“许多发展阶段是并行处理的,不像在个体治疗中发展的有序的移情平面。”治疗给予精神内部和人际世界以及群体现象应有的重视,因为这些现象不断相互影响。
另一个重点是在医院的所有变化都不是意识层面的,也不是通过语言呈现的。某些变化,或许是更有效的那些,是源于内隐的关系学习,非解释性变化(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思维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我们要总结一下医院治疗的效果,我们会用一句非洲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心理治疗性医院就是这样一个重新养育人的村庄。
临床案例......(略)
问答环节
学员提问1:这种心理治疗性的医院是综合医院加心理治疗的医院工作模式吗?
Emel:不是的,跟你说的这种综合医院加心理治疗的医院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这次讲座试图说明的一个部分。它既不同于专科医院,也不同于那种综合性医院。在心理治疗性的医院里面,它主要起作用的部分,是我们能够在医院里面去结合方方面面的人员,结合方方面面的**工作者,然后让患者跟不同的人能够发展出不同的关系模式,这个可能是对病人既往的一种客体关系的模式的修正和改变。
学员提问2:病人的费用,主要是由医疗保险支付还是自费?
Emel:在我们的医院里面,大部分的费用是由病人本人来支付的,保险能够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小,因为美国的保险体制会认为这样的治疗花费是非常高昂的,因为病人要接受非常密集且非常全面的一个治疗,所以他们并不为治疗买单,大部分是病人本人支付的。
学员提问3:这极大消耗医疗资源,如何平衡医保与病人经济能力?
Emel:其实在中国已经有这样的心理治疗性医院了,在武汉就有一家,据我所知,在中国的治疗费用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保险可以支付的,这个跟美国可能情况不太一样,在美国的话你很难找到那样的保险公司愿意为这样一种形式的治疗去付费的。而且确实比较贵,大部分的人是支付不起治疗费用的。但是话说回来,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密集的、高强度的治疗,多数的病人可能是并不需要的。所以这种治疗方式说到底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治疗形式,但是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人而言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