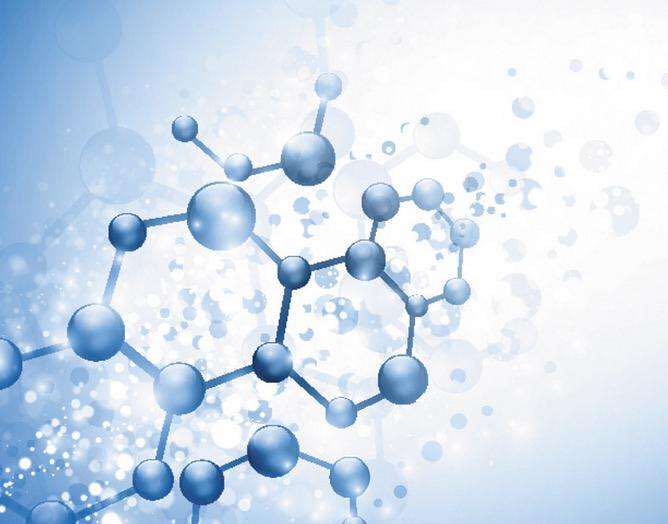印藏佛学中的主体间性
正如在“有分识”即觉知的基础状态中,“认知”和“慈心”携手共存;同样,在灵性成熟之路上,智慧之光和爱心之温热必须同时培育。在佛教传统中,“四无量心”的修法,是对“四念处”的补充。“四无量心”,即: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4。 这些情感形态,极易和其他几种情绪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似是而非。为有助于区分这些情感形态及其赝品,不妨吸取一下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建言,他在其经典著作《我与你》(Buber, 1937/1996)中提出几类不同的关系。 先看一下马丁所说的“我——它”关系:一个人对待另一有情,如同一件物事,随己心愿而任意操纵。在此关系中,一个人完全漠视“他人亦为主体,和我一样”的事实,或者将此事实压减到*低限;在其眼中,“他人”(不如说“它”更合适)无非是下述三者之一:或者有助于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或者会成为一种障碍,或者无关痛痒。由此出发,这人将被视为朋友、敌人或无足轻重之人。在“我——它”关系中,其实只有一个主体,即“自我”;然而,随着“他人”被明显地剥夺人性色彩,一个人自身的人性色彩也悄悄褪去。 与此相反,“我——你”关系的实质,则是对话性的;它意味着一个人真正融身于另一个人的“主体实相”中。“我——它”关系,乃是操控性的实质;“我——你”关系,则为真正的主体间性,故此它立足于一种“同情共感”。据布伯所言,在“我——你”关系之中,一个人会超越自他两极,融身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域”;在此域中,两个主体都步入超越个体的“永恒之你”。这一“永恒之你”难觅其门,除非两个主体都置身于“我——你”关系中。它本性中,乃是一种参与性体验,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实现。 起源于犹太教——基督教及希腊——罗马传统两大渊源的西方思想,在面对主体间性关系时,主要乃是“人类中心主义”。相反,如前所述,佛教则被视为“生命中心主义”,因为它强调的核心,是一切有情,而非仅限于人类。四无量心的修法,意在培育“慈”等四心,使这些健康情感臻于如此境界——超越一切界限和划分。 四心中*先培育者,乃是慈心,它被理解为“真诚期盼他人获得幸福”。慈心的梵文术语“maitri”,极有可能被简单地译为“love”(爱),但通常并不这样处理;这是因为在英语中,“love”一词难以区分“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佛教修法培养的“慈心”,其重心蕴含于一种“我——你”关系之中,行者可以清晰地觉知他人的快乐和悲伤、希望和恐惧。而英文的“love”一词,还适用于性恋、个人依恋,乃至“深受非生命物质和事件吸引”等等情况——这些都涉及“我——它”关系。佛教中通常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术语——“raga”(贪),来指称这类形形色色的吸引力;在不同场合,它也可以译为:“耽爱”(attachment)、“贪求”(craving)、“痴迷”(obsession)。 根据佛教,“耽爱”者为某一对境吸引,他于意念中添加或夸大对境的怡人品质,过滤掉不甚满意之处。当“耽爱”日益强烈时,一个人的自身幸福完全系于所倾心的对境之上,从而丧失了自主性而交付于臆想的对境。即便这一“耽爱”的对境乃是一个人,它也体现为“主体内”(intrasubjective)而非“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关系,因为耽爱者沉溺于自己臆想的对境,而非将其作为真正主体来交往。 一旦真相(即理想化对境的所有过失和局限)打破了耽爱者的幻想,幻灭即随影附形而来。继而,反会引生敌意和厌恶,因为此时,耽爱者又添加种种负面品质于他先前如此珍视之人。 所以,如佛教所言,“慈心”不会轻易转为厌恶,但“耽爱”会。“慈心”乃是一种健康的情感,对自他幸福皆有助益;“耽爱”却是焦虑、痛苦和人际冲突的主要根源。因此,区分二者非常重要;但是,在绝大多数亲密关系中,比如亲子、配偶和朋友关系之中,这二者常常混为一体。在这些复杂的人类关系中,佛教的理想是减少“耽爱”的烦恼,培养健康的“慈心”。 在佛教的传统修行中,行者先修习对自己的“慈心”,然后将此情真意切的关怀延伸至他人——初看起来,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其原理,源自佛陀讲述过的一个基本原则:“真正爱己者,恒时不会伤害他人。”(《自说经》,Udana,47) 这一策略,似乎特别适用于现代西方社会;在如今的西方,自轻自贱、缺乏自尊、内疚,或自认为不配获得幸福等等,这一类感受似乎达到了流行之地步5。在真实的禅修中,行者先行思维自己对幸福的向往以及远离痛苦的心愿,由此生起慈愿:“愿我能离于仇恨、痛苦和焦虑,幸福地生活。”和“正念处”的前行修法类似,这一修法蕴含了一种“我”的他异性:行者将自身视为对境,然后为其祈祷,“愿你吉祥幸福”;如此,行者步入和自身的一种“我——你”关系之中。 在此修法的下一步,行者思忆某一钟爱和敬重之人。当念及此人的善举和美德时,行者生起诚挚心愿:“愿此善良之人,如我一样,吉祥幸福。”如此继续修习,行者依次思忆一位深爱的朋友,之后是一个无关痛痒之陌路人,*后或许是一个自己憎恶之人。这般修习的目的,在于逐渐体验:如同慈爱自己一般慈爱好友,如同慈爱好友一般慈爱陌路人,如同慈爱陌路人一般慈爱敌人。以此方式,横亘于朋友、陌路人、仇敌之间人为的“我——它”栅栏被打破,行者或将体验到无量的,无条件的慈心。 如前所述,“耽爱”乃慈心的赝品。依据佛教,慈心的反面乃是嗔恨,而非漠不关心。漠不关心可视为慈心的90度转弯,而嗔恨则是慈心的180度转身;因为,当内心为嗔恨主宰时,一个人见到他人的幸福前景,内心如实感受到不快乐。慈心的近因,乃是见到他人内心的可爱品质,而非仅仅流于外表的吸引力。在此修法中,若行者能平息敌意,修行即为成功;若修行仅仅导致了自私的爱恋或耽执,修行即告失败,因为这意味着行者仍然受困于“我——它”心态之中。 四无量心中的第二个是“悲心”,它与“慈心”密不可分。生起慈心的人希望他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幸福之因,而生起悲心的人则希望他人能够远离痛苦和痛苦之因。这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如“耽爱”常常和“慈心”混淆(特别是当它们都被称为“爱”时),对他人的“义愤”很容易和“悲心”混淆。如果一个人的“悲心”仅仅泽及世界上的“受害者”,而没有包括“施害者”,这一“悲心”其实仅仅是对受欺压者的“耽爱”,同时还伴随着对欺压者的憎恶。换而言之,此人依然陷于“我——它”心态中。 佛教的悲心修法,不仅关注那些正在经受痛苦之人,也关注那些种下未来痛苦种子的人——即伤害他人之人。依据佛教教义,世上所犯下的一切罪恶都源于贪爱、嗔恨,以及二者背后的愚痴。这些破坏性的倾向,被视为“烦恼”,即心灵上的折磨,它们与肉体上的折磨非常类似;而被“烦恼”左右的人,比身受疾病折磨的人,更值得“悲心”的怜悯。但是,对作恶者生起悲心,并非宽恕他们所造的恶。而是愿这些造恶之人,能够远离种种“烦恼”——驱使他们行此伤害的冲动,从而远离种种痛苦之因。 在培养悲心的禅修中,行者首先思维某个不幸和悲惨的人,并且发愿,“但愿此人从痛苦中解脱”!随着禅修的深入,行者依次思维一个造恶之人(无论其眼下是否幸福)、一个亲近之人、一个陌路之人,*后是自己憎恶之人。如此修习的用心,与慈心修法一样,意在打破隔开不同类别之人的栅栏,直至行者的悲心平等泽被一切众生。 “悲心”的赝品乃是“悲伤”。在英文中,“compassion”常常在口语中表述为“我为那人感到难过”云云;但根据佛教,仅仅为某人感到难过,不一定会引生悲心。当一个人感同身受地关注另一个人的不快乐,他自身自然会体验到忧伤。但这一感受也许反而会引发“义愤”和报复之心愿——惩罚那些使他人痛苦之人。与其相反,在悲心的修习中,因移情而感受到的忧伤或悲哀,成为给悲心供暖的“燃料”。行者不只是流连于忧伤与绝望之中,而是于中生起如此心愿:“愿你远离此苦及苦因”!行者从当下的痛苦现实中转身,迈向解脱此痛苦的可能。因此,移情共感的忧伤,乃是悲心的催化剂,但非悲心本身。 “悲心”之反面,并非冷漠,而乃“残忍”。当此烦恼主宰人心时,一个人会于不知不觉中认定他人的主观现实,并有意识地希望他人体验痛苦。这被广泛视为摧垮人心之*极大恶。“悲心”的近因,乃是见到那些被痛苦及苦因淹没之人的无助。在此悲心修法中,行者自心的残忍习性若是消退,修行即为成功;如若仅仅生起悲伤,修行即为失败。尤需强调的是,佛教之慈心与悲心禅修,其本意绝非是取代“乐于助人”的行为。确切地说,它是这类利他行为的一种内心准备——正是如此的内心修习,才源源不断流淌出类似的外在利他行为;外在的利他行为,其实正是内心仁慈与关爱他人幸福的表露。 如若行者的慈心与悲心修习圆满,则四无量心中的*后二者无需勤作即可获得。如若一个人对他人怀有慈悲心,然则,当他人体验快乐时,其由衷的反应即是“感同身受地欣悦于他人之乐”。但此“喜心”也有自身独特的修习之道。在佛教禅修技巧中,行者首先专注于某个常常喜笑颜开的亲密友伴,之后为某一陌路之人,*后延及一个憎恶之人。每一次,行者都驰骋想象力,深入他人的快乐之中,如同体验自己的快乐一般去体验它。与此同时,行者的“喜心”,或许会仅仅停留于他人肤浅的幸福表象,但这正是“喜无量心”的赝品。这一健康情感的负面乃是“嫉妒”,而其近因乃是觉知到他人的幸福与成功。若修行中仅仅生起肤浅轻佻之心,此时的修行即为失败。 第四“无量心”,即“舍心”,其实遍布于其余三者之中——当行者打破自我中心的种种分界,不再强加于人时,“舍心”即在其中。当入于“舍心”之时,行者的慈心与悲心平等地泽被他人,不分敌友。这一“舍心”以“同情共感”为基石——了知在幸福面前,一切有情都和自己一样,皆应平等。这一禅修,从思维一个陌路之人入手,之后是亲近之人,*后是憎恶之人;每一次,都安住于“等舍(即平等无别之心)”之中,远离耽爱或憎恶。 愚蠢的冷漠是此处所修“舍心”的赝品——“冷漠”使人对无论何者的幸福,皆漠不关心。舍心的反面,乃是对所爱之人的耽爱,以及对敌人的憎恶;其近因,据说是为自身行为担起责任。若行者体验到一种平等心(这是生长慈心与悲心的丰饶大地),修行即为成功;若修行中仅仅生起了冷漠,即告失败。 在印藏佛教传统中,有一种经典修法,将慈心与悲心的修习融为一体;这一修法,在藏语中名为“tonglen”(施受法),意思是“给予和接受”6—— 此中的“给予”成分即为“慈心”修法,而“接受”成分即为“悲心”修法。 “接受”部分的修要如下:首先,清晰观想一个所爱之人,一群人,或其他有情,观想他们正在经受痛苦或者因造作恶业而播下苦种。行者以“同情共感”入于此人的痛苦或苦因之中,由此产生如此心愿:“愿你不再承受这一重担,愿此不幸成熟在我身上。”无论是痛苦还是逆境、身体还是心理的,行者都观想为一团黑云,离开他人身心,被自己吸纳,入于自心中。如此观修之后,进而观修此人逐渐脱卸负担。一旦黑云进入自心中,行者即观想它与自心中状似黑团的“自我中心”意识相遇。瞬间,痛苦的黑云和黑体状的“自我中心”意识,相互湮灭,都未留下任何痕迹。 在此修法的“给予”部分:行者观想,自己一生的所有荣华、幸福和贤善,化为自心中一个迅猛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灿烂的白光。行者观想这些炫目的光芒投射并融入此人,同时发愿:“我生命中的一切美好、我的财富、我的幸福、健康,我的德行,都给予你。愿你吉祥幸福。”于此同时,行者观想这些美德和幸福之光弥漫于所忆念之人,观想他或她的*有意义的欲求和心愿都得到了满足。这种自内心流淌出来的光芒无有阻碍,也不会枯竭,因为在观修中,它来自于一个取之不尽的源头。 当行者对此观修熟悉之后,他可以扩展觉知的范围,*终遍及一切有情,吸纳所有痛苦和烦恼,并布施自己的一切美德和善意。这一修法可以与呼吸配合:每一次吸气时,观想吸纳苦与苦因之负累;每一次呼气时,观想自内心放射白光,将快乐与快乐之因带给整个世间。 这一修法源于公元八世纪的印度圣者寂天菩萨的著作,他在著作中总结了这一修法隐含的原理:“我应除他苦,他苦如自苦。我当利益他,有情如我身。”(Shantideva,1997, VIII: 94)。这是一种与一切有情的“我——你”关系的纯粹表达。佛教修行所培养的“我——你”关系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佛陀”之尊名,意为“清醒觉悟者”,其寓意是:未成佛之人,都在睡梦之中;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与不清明的梦非常相似。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根据中观学派(Madhyamaka)的观点,醒时体验有一种如梦如幻的品质,因为事物的“显现”与事物的“真实存在”大相径庭。一切现象(自己、他人,以及体验之境中的所有其他事物),看似各赋内在实质,而独立于对其解读的概念框架。但是根据它们的“存在”方式,一切“有为法”(conditioned phenomena,即因缘和合而生的现象),都依赖于: (1)先前的因缘, (2)自身的组分和属性,以及 (3)名言概念——依靠名言(名称),它们得以和其他现象区分,并“拥有”了自己的组分和品质。 简言之,自他有情,以及其他所有现象,看似都是凭自力而存在,并有独立的自性;但是,实际上,没有一样事物之中,能找到这样独立自存的实体。根据中观学派的论点,万法皆无自性,即名为“空性”7。 对此,14世纪西藏中观派哲学家宗喀巴大师说:“虽然觉知的对境,永远彻彻底底地找不到一个终极自性或客观实体;但毫无疑问,它们在显现中看似具有真实,内在实有的自性。……这些事物,一如既往地循着相互依存和因果律的法则运行。”(Mullin,1996,p.174)。根据这一观点,似乎可以推断:觉知的对境(颜色、声音、香味等等),在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它们并非离于觉知它们的感官形态而独立自存。但是,中观派的见解决非如此简单,而是比此更为微妙。例如:树,一旦离开了我们对树的知觉,还存在吗?中观派的回答是:树,以及自然界中很多其他对境,确实存在,并独立于我们的知觉。在无人目睹时,花继续生长和开放;而无论是否有人亲眼见证这些事件,树都会坠倒在森林中,在空中和地面上激起涟漪,随后开始腐烂。 人们可能会问:“花草树木,还有其他自然现象,真的独立自存,不依于任何赋之其上的名言概念吗?”对此的回答是:“花草”、“树木”等等词语,离开了我们赋予它们的定义之后,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因此,这一问题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就此追问:“是否存在任何独立于人类语言和思维的事物?”这一问题隐含了一层暗示:“存在”一词,某种程度上乃是“自定义”,它独立自存,不依赖任何约定俗成的定义。然而,像“主体”、“客体(对境)”、“存在”、“参照”、“意义”、“理性”、“知识”、“观察”和“体验”等等,这些术语个个都具有一摞子不同用法,没有任何一词具有某个单一绝对的意义——一个优先于一切的意义。 由于这些术语并非“自定义”,当我们使用这些定义时,无法离开所选的概念体系。意即:我们选择了我们所用的定义;它们并非由客体现实所决定。故此,持中观见解者,再次总结道:这一问题没有意义——既然,“存在”一词,一旦离开所有概念性体系,自身都不再具有任何实义;那么,追问是否“存在”独立于一切概念性体系之事物,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基于这一点,中观见解反对形而上的实在论。形而上的实在论,其见解描述如下:(1)世界由独立于心智的客体组成;(2)有关世界存在之道,有且只有一种真实而完备的描述;(3)“真理”一词,涵摄某种对应关系——一个独立自存的世界和对它的描述之间的某种对应8。在这一点上,*先为中观哲学建立体系的二世纪印度哲学家龙树尊者(Nagarjuna),也许会赞同二十世纪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声明:“我们观察到的,并非是自然本身,而是曝光于我们提问方式下的自然。”(Heisenberg,1962, p. 58)科学家们探询自然之道,乃借助于和工程师携手创制的测量仪器。但是,由此仪器收集而得的数据,既有赖于所研究的客体现象,又取决于测量仪器本身。 因此,这些数据的产生,有赖于各类相关事件;这一点,正如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源自不同振动的交互作用,既包括某种客观介质的振动,也包括我们听觉器官的振动。同样,正如我们听到的声音并非独立自存于客观世界之中,任何由技术仪器搜集的其他数据也是如此。 形而上实在论的支持者,可能会坦然承认这一点,然后反驳道:物理学的概念世界的确存在,它以客观量为基础,和真实的客观世界相对应;后者独立自存,不依赖语言和思维。 然而,针对这一点,爱因斯坦表示了担忧:“……原则上,试图仅以可观测的量为基础,来建立一种理论,这是非常错误的。现实中,事情往往正相反。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测到什么。”(转引自Heisenberg, 1971, p. 63)当科学家解读采自测量仪器的数据时,他们必须区分“有意义的数据”和“噪音”。他们采用的理论,在行抉择之时,扮演了一种工具性的角色;在决定制造何种测量仪器,以及如何解读由此采集的数据时,事情同样如此。*终,被“观测到”的数据,深受“理论渗透”。 因此,依靠感官或技术仪器测得的“觉知对境”,它们的存在,不仅无法独立于这些探测途径,同时也无法独立于对此探测施行筛选的概念性框架。此外,物理学家们所构思的理论元素,自身亦是作为相关事件而生成——它们的肇始,既有赖于观测数据,也有赖于解读赋义这些数据的科学家们的概念性智能。这意味着,知觉体验和概念体验一样,同样具有“主体间性”本质;尤其在考虑到概念框架的约定俗成天性时,事情更是如此。 这不仅在一些量子理论创建者的思想和中观见解中找到一些相似之处;与此同时,也在当代哲学思潮中找到了一些知音——普特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或许和中观见解*为亲近。普特南的一次陈述,和龙树的观点相当吻合:“我们称为‘语言’或‘心智’的元素,渗透于所谓‘现实’之中,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解读自身的一些努力,从一开始已命中注定陷于‘妥协之地’——在这些努力中,我们力图将‘自己’图解为某种‘独立于语言’的事物。”(Putnam, 1990,p.28) 一旦离开了语言使用者,也就不存在任何真实性、任何意义或任何参考价值。因而,如此丰富且日益增长的世界真相之大成(指科学发现等),其实不过是经验世界的产物,而此经验世界和语言使用者交织一处,难分难舍;后者,即语言使用者,在造就我们的世界知识时,扮演了创造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