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大师荣格视角下的《易经》是什么样子?(上)

我不懂汉语,也从未去过中国。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要找到通向这部巨著(它记录了中国人的思想)的正确途径,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如此全然地殊途,要想懂得这部著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就绝对有必要丢掉身上的某些西方式偏见。
迄今,我们还一直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为了证明自然规律具有屡试不爽的有效性,就必须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而在自然状态中,事物的模样则完全不同。此时,每一过程都局部地或整体地受到偶然性的干扰,以致在自然环境中,种种事件的进程要完全符合自然规律,反倒几乎成了一个例外。
中国人的心灵,就我在《易经》中看见的那样,似乎完全关注着事件的偶然。我们所谓的 “巧合”,似乎正是这一奇特心灵的主要关注之所在。相反,在我们这里备受尊崇的因果法则,却几乎完全不为他们所注意。
我们必须承认:巧合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巧合带来的麻烦和危险,人类付出了无量的努力,然而与巧合造成的实际结果相比,因果性的理论却往往显得苍白。不错,我们可以说水晶石是六角形的;只要我们见到的是一块理想的水晶,这种说法就完全正确。然而在自然界,却不可能找到两块完全一样的水晶——尽管它们都的的确确是六角形的。
中国的圣人似乎更关注事物的实际形式而不是理想形式。对他们来说,自然规律的繁富构成了经验的现实,其意义更胜于对种种事件所作的因果性解释。何况,为了对这些事件作因果的处理,通常都必须将它们彼此分离。
《易经》看待现实的方式,似乎很不符合我们的因果关系口味。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实际观察到的瞬间情境,更多地是一种 “机遇性命中 ”,而不是可以从因果链条上得到明确说明的结果。其兴趣之所在,似乎更是种种机缘在观察之瞬间形成的概貌而不是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巧合原因的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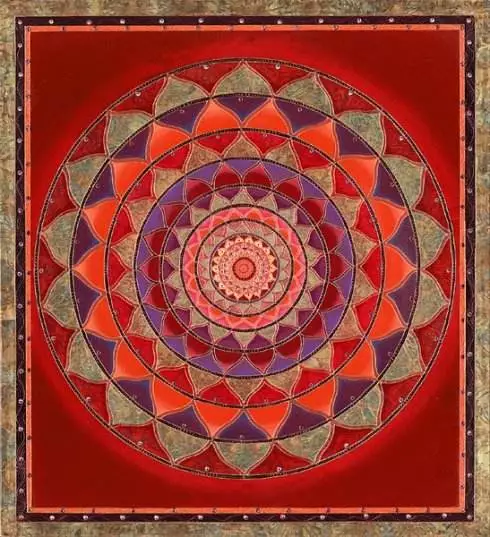
当西方人小心翼翼地进行着筛滤、权衡、选择、分类、隔离等工作时,中国人的视野却囊括了所有的一切乃至*微小、*无稽的细节,因为观察到的瞬间情境正是由所有这些成分所构成。
于是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某人掷出三枚钱币或拨弄四十九根蓍草时,种种偶然的细节便进入整个画面之中并构成其中的一个“成分”。对我们来说,这一成分是了无意义的,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它却具有极大的意义。
对我们来说,宣称在某一特定瞬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一瞬间的特性,这种说法,至少从表面上看,必然是一种枯燥乏味的无稽之谈。然而上述说法却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主张而是非常实际的情形。
有些行家只须根据酒的色泽、味道和外观便可以告诉你此酒的产地和酿造的年代;有些古董家只须随便瞄上一眼,就能以难以置信的准确,说出某件家具、某件艺术品的产地和制造商;有些星象家甚至能在事先完全不知道你的生辰的情况下,便说出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太阳和月亮的位置何在,以及黄道带在地平线上是什么标记。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特定的瞬间可以留下持久的痕迹。
换言之,《易经》的作者相信在某一特定瞬间出现的卦象,必然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性质上与该瞬间有着彼此契合的关系。在他看来,特定的卦象代表了特定的成卦时刻——甚至比钟表上的小时和日历上的月日更能代表这一时刻,因为该卦象已被视为代表了成卦那一时刻的基本情境。
这一假设牵设到一个奇妙的原理——我曾称之为“同时性 ”(synchronicity)。由此而形成的观点恰好与因果性相反。由于因果关系仅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真理而非绝对真理,它关于种种事件如何由一个衍生出另一个的假说,便仅仅是一种工作假说。而同时性则把种种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视为不只是纯然的巧合——换言之,客观事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的主观心理状态之间,存在着奇妙的相互依存 。
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沉思,其方式颇有些类似现代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家无法否认:他的世界模型完全是一种心理结构。微观的物理事件中包含着观察者的观察,恰似《易经》中的现实在其瞬间情境的整体性中包含了主观的心理状态一样。正如因果关系描述了种种事件的前后相继,在中国人心目中,同时性原则也处理了种种事件的契合和符应。
因果论的观点把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告诉我们:D的存在,是起源于先D而存在的C,C则来源于在它之前的B。与此相应,同时性观点则试图用事件的契合制造出同样有意义的情景。它试图告诉我们:A、B、C、D是如何同时出现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的。
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心理事件AB与物理事件CD有着同样的性质,其次则因为它们都是同一瞬间情境的组成部分。而该情境则被假定为代表了一个可以辨认、可以把握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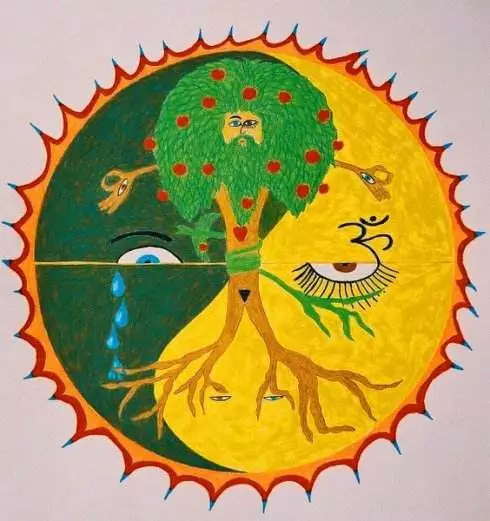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代表了六十四种彼此不同 、却各有其代表性的典型情境。借助于卦象,这些情境的意义得以确认。卦象的诠释与因果性的解释相当。事件的因果关联可以从统计上得到确认并接受实验的检验。而情境则是独一无二、无法重复的。就此而言,同时性原理似乎不可能在普通条件下用实验来检验。
在《易经》中,同时性唯一的有效性标准,是观察者认定卦辞确实显现了他的心理状况。钱币的落地、蓍草的成卦,被假定为某一特定“情境”中只能如此的事情,因为发生在该瞬间的任何事情,都作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从属于该瞬间。
一把火柴被扔在地上,形成的图案便代表该瞬间具有的特征。但如此明显的真理要显示出它的意义,则只有是在图形能够被读解,诠释能够被证实的情况下。这一方面取决于观察者对主观和客观情境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后续事件的性质。
显然,此程序不是一个习惯于用实验来检验事实和习惯于获取事实证据的批判性头脑所能接受的。但如果有谁愿意从古代中国人的角度观察世界,《易经》对于他就会有某种吸引力。
以上的论证当然从未进入过中国人的头脑。相反,按照古老的传统,蓍草之所以能提供有意义的答案,乃是“神灵”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在干预。这些神秘的力量,似乎形成了此书有生命的灵魂。
由于《易经》被视为有灵的存在,传统上便假定人们可以向它提问,并可望获得合理的回答。于是我突然想到:看一看 《易经》是怎么运作的,对初入门的读者也许是很有趣的事情。我因此完全依照中国人的概念作了一项实验:我把这本书人格化了,我要求它就它目前的处境作出判断——判断我打算将它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努力会有什么结果 。
尽管这种处理方式正好在道家哲学的前提内,它在我们眼中却显得极其古怪。不过古怪的事情即使如疯子的幻觉或原始人的迷信也从来没有吓坏过我。我总是试图不怀偏见、充满好奇地看待一切——正所谓“乐新而不疲”。为什么不冒险与这据称有灵的古书作一次对话呢?它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读者则可以见识到一种在漫长的中国文化中被反复运用的心理学程序,此程序无论对儒家还是道家,都代表了*高的精神权威和哲学奥义。
我用了投掷钱币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第五十卦,即“鼎”卦。

要与我提问的方式相应,卦辞和爻辞就必须被看做仿佛是《易经》亲自在说话。也就是说,它将自己描述成一只鼎——内有熟食的祭器。这里,食物须被理解为精神性的滋养。对此威廉是这样说的:
“鼎,一种仅为优雅精致的文明所拥有的器物,在这里暗示才能之士的自我修养,这样做对国家是有利的……这里,我们所见之文明在宗教上已达到巅峰。鼎的作用是向神奉献。神的*高旨意显现于先知、圣人。尊敬他们就是尊敬上帝。神的意志通过他们显现,人们应该以谦卑的态度来接受。”
与我们的假设相关联,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易经》是在为自己作见证。当任何一卦中的任何一爻具有“六”或“九”的价值时,便意味着它被特别地强调,并因而具有重要的含义。在我卜得的鼎卦中,神灵把“九”的强调给了第二爻和第三爻。爻辞是这样说的:
九二:鼎里有食物,我的同伴嫉妒我,但他们无法伤害我。好运。
《易经》这样说它自己:“我容纳着(精神的)营养。”由于分享到伟大的东西总是会招来嫉妒,交加的嫉妒之声便构成整个情境的一部分。嫉妒者想夺走《易经》拥有的伟大,即是说,想夺走它的意义,毁坏它的意义。但他们的恶意,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鼎的丰富意义得到了保证,也就是说,人们相信它的正面建树,没有人能够把它抢走。爻辞继续说:
九三:鼎的把柄已更换。人的生命之途被阻断。肥美的雉鸡没人吃。一旦下雨,必有悔恨。*终仍然是好运。
鼎的“把柄”是鼎上可以“把捉”的部分,它因此意指人们用以理解《易经》中鼎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概念显然已经改变,以致我们今天已经把握不住《易经》的意义。)于是,“人的生命之途被阻断”。我们不再从神谕的睿智和洞见中获得支撑,在命运的扑朔和人性的迷离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可以穿越的道路。肥美的雉鸡是盘餐中的精华,现在也不再有人吃。但一旦干渴的大地*终再一次获得雨露,一旦这种匮乏的状态被克服,痛失智慧的悔恨便告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期盼已久的机会。
威廉的评注是:“此处描述的人,处在高度发展的文明中,却发现自己不被人理会,不被人认识。这就严重阻碍了他的影响。”这就仿佛是《易经》在抱怨自己美好的品质不被人认识而任其闲置,它怀着重新被人认识的希望来安慰自己。

对于我向《易经》的叩问,两段爻辞作出了回答。其含义既无须微妙隐晦、人为牵强的解释,也用不着不同寻常的知识。任何人只要有一点常识,就能够领会回答者的意思。
回答者是一个对自己有真知灼见的人,然而其价值却既不广为人识也不广为人知。它对自己有一种有趣的看法:它把自己视为容器:器中的祭献,是献给神灵们享用的祭食。它想象自己是神秘的容器,其作用是向种种不为人知(无意识)的元素或力量(这些元素或力量已向外投射成诸神)提供精神性的营养——换句话说,是为了给这些力量以它们需要的关注,以使它们能够在个人的生命中发挥作用。的确,这正是“宗教 ”一词的本义,即细心地观察和考虑圣秘者的存在。
《易经》的方法,的确体察到了人事 (以及一个人自己无意识自性)中隐秘的个人性质。我询问《易经》的方式,就如同询问一个将要介绍给朋友们的人——我问它是否同意这种介绍。
在回答我的询问时,《易经》说到了它的宗教意蕴,说到了目前人们还认识不到这一意蕴甚至对此存有误解,还说它希望重新获得昔日的荣光——*后这一点显然表明:它瞥见了我尚未写就的序言,首先是瞥见了它的英文译本。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反应,就像一个人处在相同的处境中也会作出的那样 。
但这种反应是怎么发生的呢?不过是因为我把三枚钱币抛向空中,让它们落下、滚动直至静止不动——有时正面向上,有时背面向上。这种使意义得以发生的反应,却出自一开始似乎完全排除了任何意义的做法。这一奇妙的事实,恰恰是《易经》的*大成就。
西方思维认为:我的问卜方式可以得到无数答案。我不反对这种说法,且确实不能断言另一种回答就没有同样的意义。尽管如此,我所得到的回答,却既是**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我对其他可能获得的回答一无所知。这个回答已经令我高兴和满意。
重问同样的问题并不是高明的做法,我也没有这样去做。这正所谓“大师一语不二言 ”。我厌恶拙劣的教育方式总是试图将非理性现象纳入先入为主的理性框架的做法。
的确,诸如这样的回答,在其初次出现的时候,就应该让它保持原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自然在没有受到人的干扰时,自己会做出些什么。人不应该在尸体上研究生命。更何况,重复实验也不可能,因为原来的情境不可能重建。因此,在每一案例中,都只有*先的回答是唯一的回答。
(未完待续)
新乡市心灵港湾心理咨询中心欢迎您!电话:158387331085



